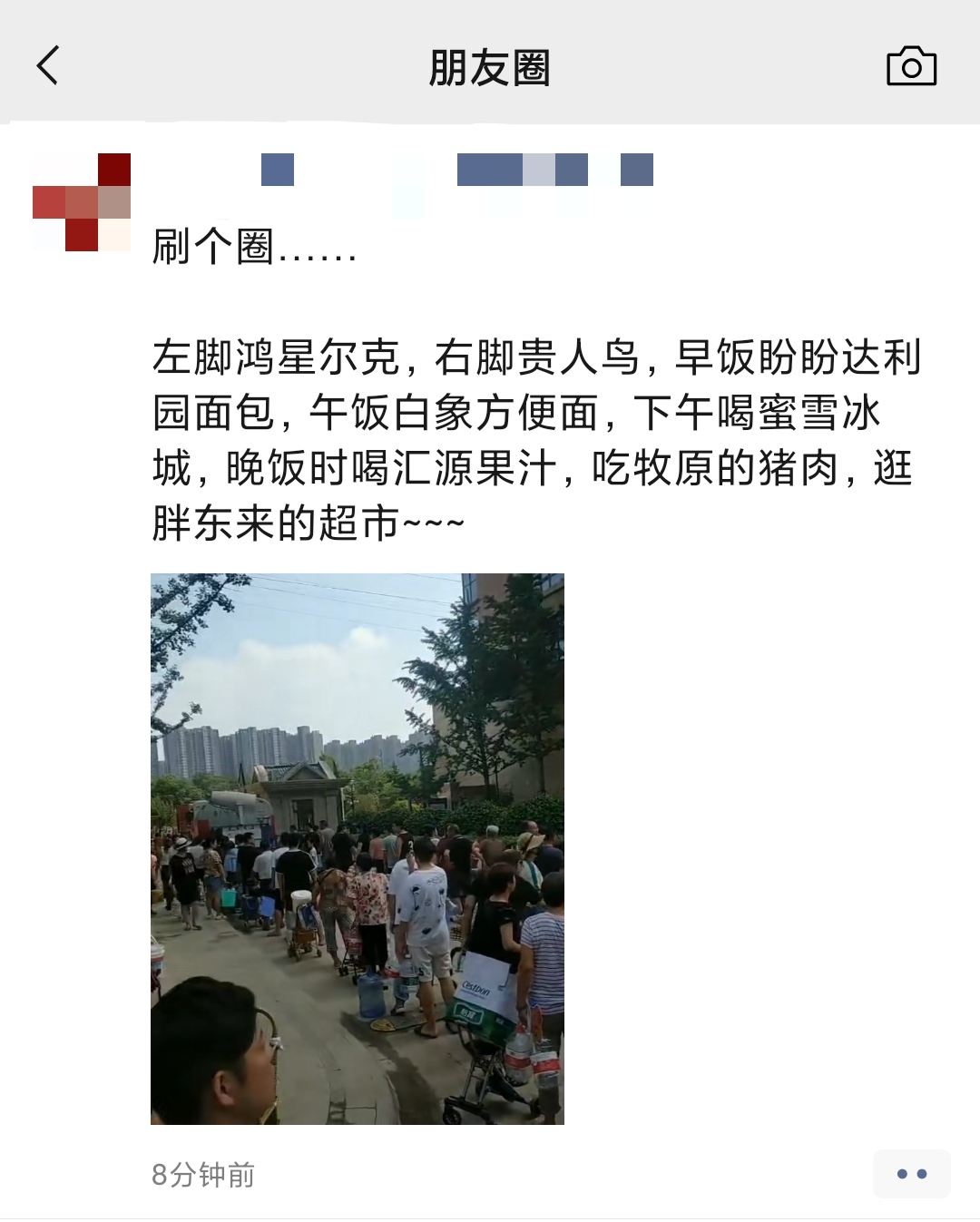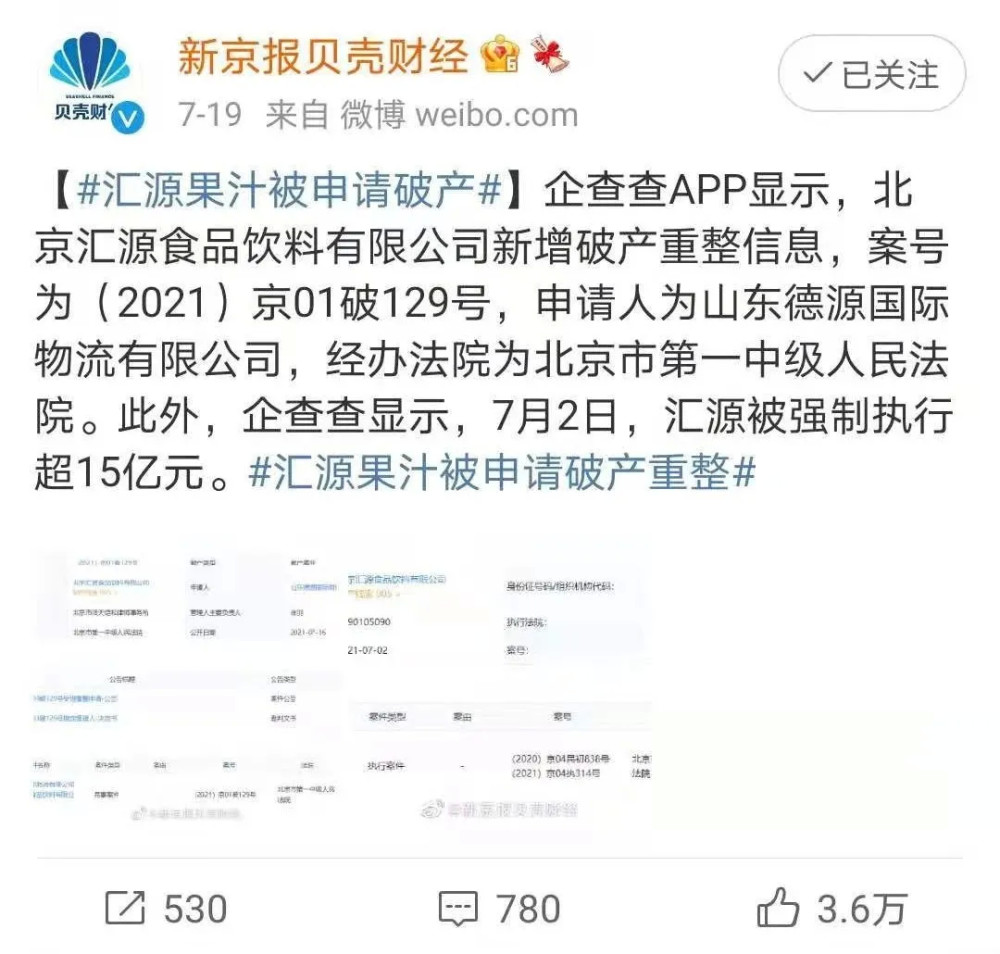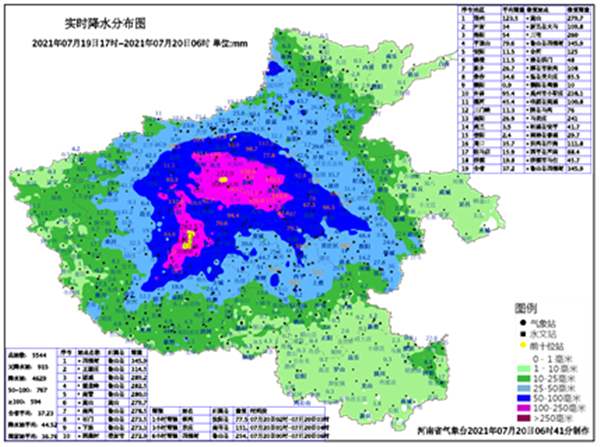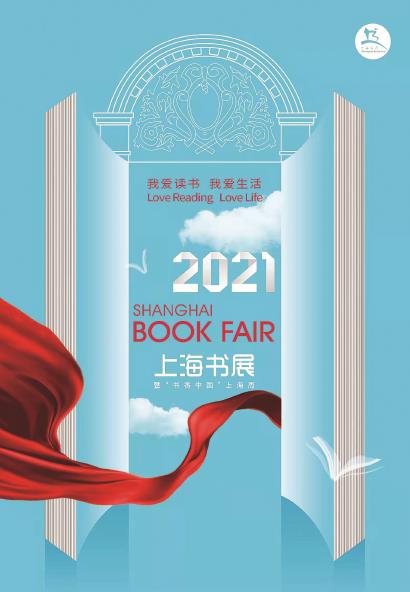建行的餐后甜点
零售业务
没有人或者组织能够轻轻松松走出舒适区,建行亦如是。
考虑到建行自身庞大的信贷规模以及资源可配置性,至少在一个可见的时间范围内,其他零售业务根本无法改变建行业务、营收乃至盈利结构。正是从这一点出发,让我们看到了建行未来的发展很可能面临“失速”。毕竟,2020年特殊的宏观环境很难再现,相比2020年货币政策边际收紧将导致建行对公类业务发展面临紧箍咒。
对于建行业绩来说,还有一个很大的威胁在于住房贷款业务将不得不做出被动调整。据2020年底央行、银保监会《关于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知》(下称《通知》)相关规定,包括建行在内的六大国有银行个人房贷业务占比控制在32.5%以内。2020年末,建行个人房贷占比35%,超出规定要求2个百分点以上。
这意味着未来几年,如果没有整体信贷规模的大幅扩张,建行在个人房贷业务上实际已经触达了业务拓展的边界,否则建行将因房贷超标面临额外的资本金要求,尽管根据监管规定,建行有4年的调整时间。属于建行房贷业务的监管红利也已经结束了。
2021年一季度的财报数据很可能大致透露了这一趋势。一季度净息差2.13%,相比2020年下降6个BP;归母净利润831亿元,同比微增2.52%,这一增速虽然高于2020年的1.62%,但是去年数据受到了拨备计提的干扰。从拨备前利润看,今年一季度实现拨备前利润1526亿元,同比增长3.42%,远低于2020年的7.43%。
从信贷规模看,一季度环比扩张5.27%,相比2020年大幅放缓;从信贷产品类别看,今年一季度建行零售贷款增长几乎停滞。财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末,建行零售贷款余额7.45万亿元,去年末为7.23万亿元,环比微增3%。
目前还不是很清楚建行一季度零售贷款增速的大幅放缓是否是上述因素的结果,但今年中报数据应该会有很好的揭示。
不少机构认为,建行的零售业务具备发展空间,并发布研报积极看多建行的零售业务布局,个中原因在于其高达2.8亿的庞大客户数量,实际上这未必一定带来竞争优势。一方面,相比城商行以及股份制银行,建行的业务下沉力度不够,这对于发展零售金融不太有利;另一方面,建行并未做好向零售业务转型的真正准备。
管中窥豹,不妨以建设银行与招商银行的App端做一个简单的对比。下图,左边为招商银行,右边为建设银行。

不难发现,建设银行的App端功能还沉浸在缴费等相对“原始”的移动互联网应用阶段,在零售业务的产品与布局方面是缺乏战略纵深的,零售业务布局较好的招商银行已经进化到了场景、圈子、生态。二者在功能上的异同最终导致零售业务上的竞争力差异是不言而喻的。
再看一个关于零售业务的细节。建行2018年提出了“零售优先”的战略,但是这一战略在2019以及2020年两年的财报中,建行不再提及。另据建行历年财报,2018年财报中31次提及“零售”,到了2019年财报,下降至29次;2020年财报,零售二字仅提及27次,频次的不断下降,某种程度上意味着零售战略地位有所下降;“住房”取而代之,其在财报中的提及频次逐年上升,2018年,为77次,2020年,为91次。
财务数据可以印证二者最终产生的效果之不同。2020年,招商银行平均存款成本1.22%,建设银行1.75%;从存款成本最低的活期存款平均余额占零售存款的比重来看,招商银行这一数据为65%,远超建设银行46%的占比。
建行的零售业务曾被外界寄予不小的期望,然而实施的效果并不理想。如果不考虑个人房贷,零售业务对于建行来说,只算是个餐后甜点。
即使退一步观察建行的“住房租赁”战略,这一战略依然面临金融切入服务业(如建行)还是服务业切入金融(如贝壳)谁更具备效率的争论。至少目前来看,截至2020年底,建行房源2400万套,去年下半年仅新增90万套。截至今年一季度,建行租赁业务注册用户3362万户,占目前租赁市场2.2亿用户规模的15%。建行并未在财报中披露涉及租赁业务的消费信贷金额。
一个小小的细节也暗示建行做大住房租赁业务难度不小。打开建行App,找到建融家园,打开第一个整租,《红周刊》记者亲自测评发现,全北京区域提供的房源合计76套(截至5月21日),房源少的可怜。在App的使用上,记者如果点开某特定的房源链接后,是无法退回到上一级页面的,只能关闭后重新搜索,用户体验极差。建行拿什么跟贝壳、我爱我家等展开市场竞争?如果这也构成金融科技的一部分,那么只能说构成建行“第二增长曲线”的三大战略之一的“金融科技战略”远不够夯实。
但凡伟大公司成就的构建都是建立在细节基础之上的。
建行需要回答的问题还有很多。比方,如果房贷停滞,建行将如何重新有效配置自己的信贷资源?建行能否承受普惠金融下的高不良率?零售金融乃至普惠金融的获客如何解决?等等。
住房金融如果不能获得突破,对于建行来说,结果很可能只有一个:所谓的“第二曲线”大概率跟随“第一曲线”。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