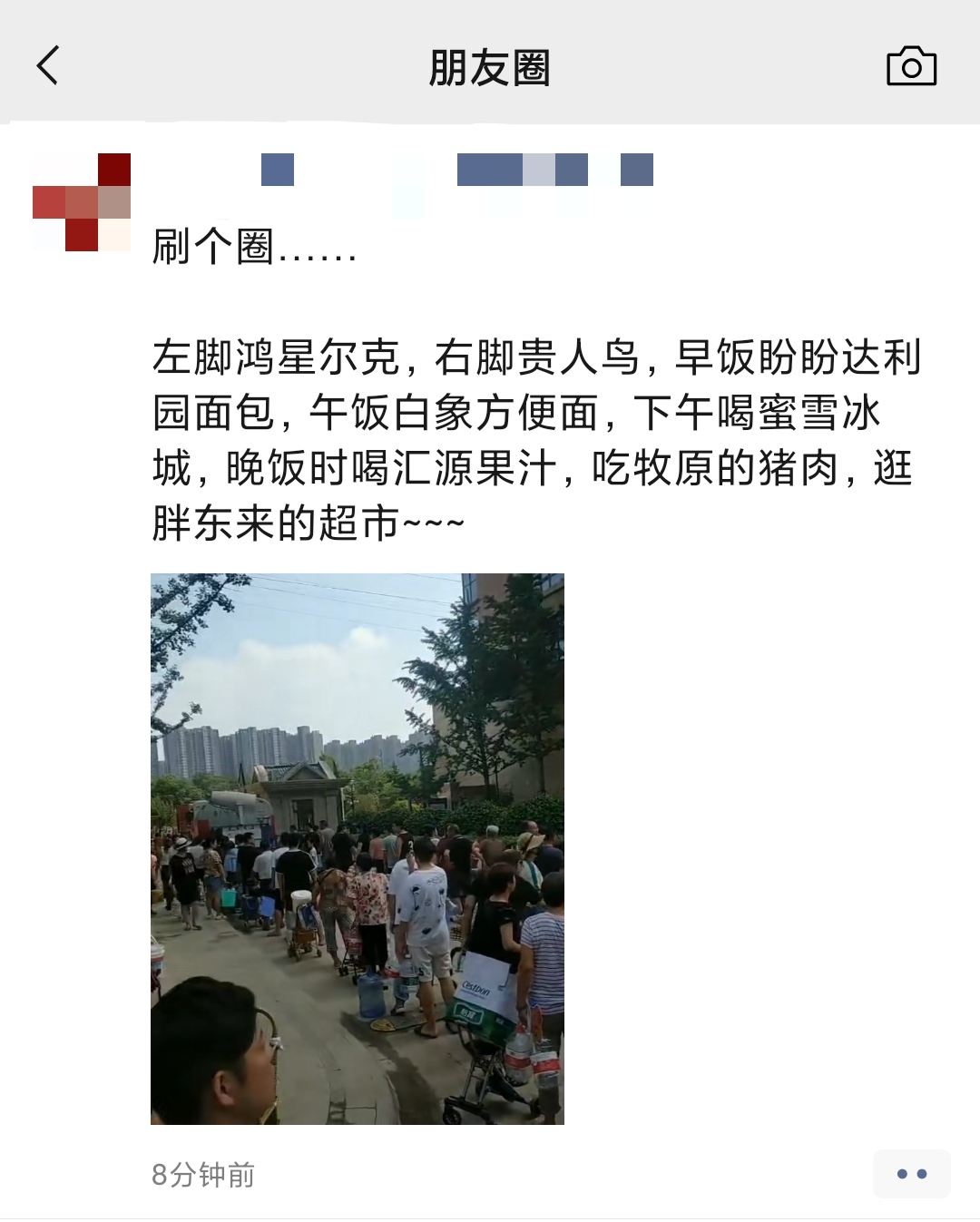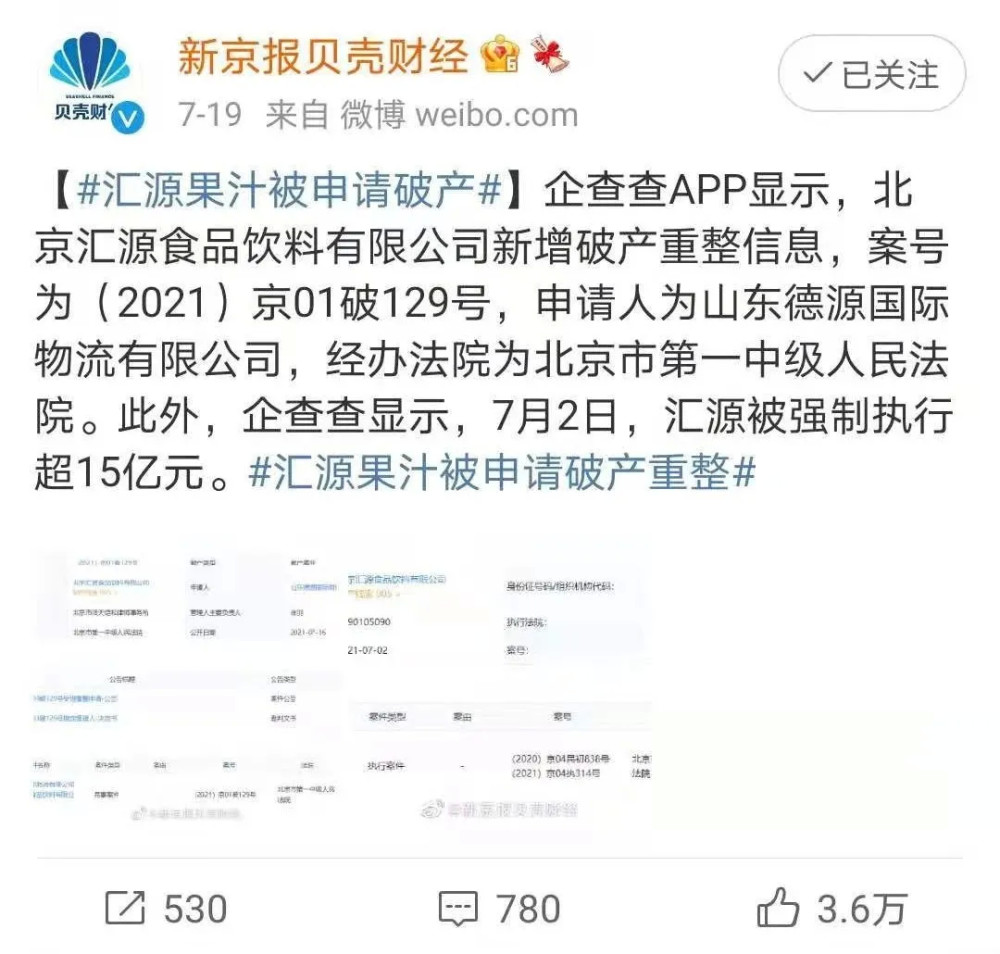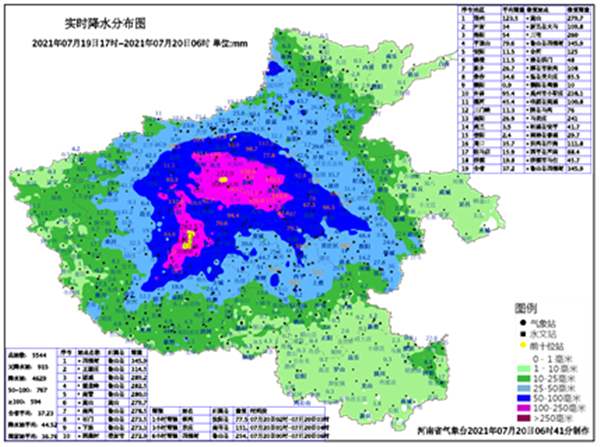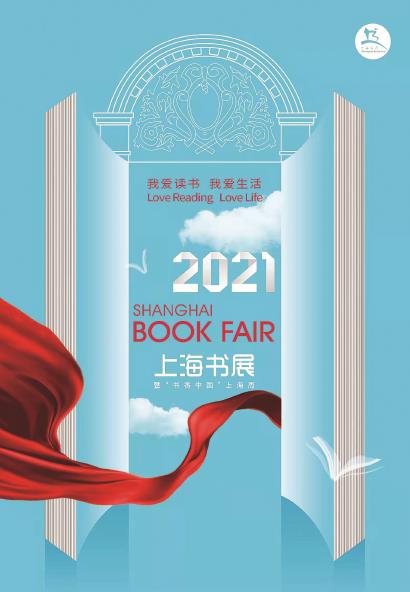零售业务缺乏纵深
赚钱全靠房贷
建设银行的净息差之所以跑不过同行大多数竞争对手,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资产端收益率的制约。
财务数据显示,建设银行平均生息资产收益率3.77%,远低于行业4.6%的收益率平均值,部分规模较大的区域性银行、股份制银行能够获取4.5%以上的收益率。不过,就国有银行而言,工、农、中、建、交五大国有银行这一数据大体持平,另外一家国有行邮储银行的数据相对高一点,也只有3.97%的水平。
较低的生息资产收益率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客户结构。国有商业银行,尤其工农中建四大行,主要服务于国有企业等大型甚至超大型客户。相对来说,这些客户质地不错,这也意味着包括建行在内的商业银行议价能力相对有限,尤其在利率市场化的环境下;在更加具备议价能力的中小微客户以及零售客户方面,建设银行布局不足,这限制了其息差走阔的能力。
某种程度上,建设银行过去很多年的发展靠的是政策红利以及国有大型企业。受益于巨额不良贷款向财政的剥离,实行了商业化改革的建设银行得以轻装上阵。再加上房地产、基础设施的跨越式发展,建设银行在2007年上市以后的多年里,一直维持着业绩的高歌猛进(不含2008年金融危机),中间发展最快的年份业绩增速甚至超过了50%。考虑到建设银行的巨额资产体量,这一发展速度是惊人的。
转眼到了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层面出现了一件大事,“蒜你狠”、“姜你军”,“苹什么”轮番上演。过热的经济格局以及过高的货币投放导致中国出现了高达6%的严重通货膨胀,货币政策不断收紧,信贷投放随之下滑,这一年也成为了建行业绩的重大转折点。

2012年,建设银行的业绩增速呈现断崖式下跌,当年其归母净利润增速14.13%,是2011年的一半多一点。此后,这家银行的业绩发展速度就开始明显下降了,整体维持个位数偏低的增速直到2020年,中间个别年度的业绩甚至是负增长,且中间伴随由于流动性收紧而导致的不良贷款率攀升。

属于建设银行的政策红利时代结束了,周期让位于消费,商业银行迈入零售金融时代。来自中央层面的结构性经济调整政策驱动中国商业银行转而进入艰难的调整与转型期。
转型哪有那么容易。过去随随便便依靠放贷规模便可以取得的辉煌业绩,实际是时代给与的红利,这更加彰显后续转型的艰难。
此后的多年里面,建设银行一方面耐心的处理着其账面过去多年累积起来的不良贷款;一方面艰难的寻求向零售的战略转型,探索“第二增长曲线”。以过去两年为例,建行清理不良贷款就高达1382亿元,迄今为止其账面不良贷款余额依然超过2600亿元。
“第二增长曲线”是建行董事长田国立于2019年提出来的,其核心在于通过B端赋能、C端突围、G端链接,开启转型和重构,重新定义新时代银行的功能,本质在于发展零售业务,并重塑建行业务增长点。
但是建行的转型在业务层面遭遇挑战。2018年建行提出零售优先战略,实际进展不大,缺乏纵深。至少从2020年的业绩来看,建设银行的发展是靠两条腿走路,一方面靠对公业务维持和扩大市场规模;一方面依赖房贷猛赚钱。
市场规模方面。2020年,建行以16.7万亿元的信贷资产规模位居行业第二,同比增长11.73%,驱动这一业务增长的主要是对公类信贷业务。财务数据显示,建行2020年对公类信贷余额8.4万亿元,业务规模仅次于工行,对公信贷占比50%,同比增长超20%。零售业务贷款余额7.2万亿元,占比43%,同比增长11.7%,低于对公业务发展速度。
零售业务方面。乍一看建设银行的零售业务占比颇高,市场规模也很大,实际全是房贷驱动。2020年,建行房贷余额5.83万亿元,同比增长9.9%,房贷业务贡献零售贷款超过8成。
过去十年,建行个人房贷余额增长超过5倍至5.83万亿元,十年复合增长率18%,超过信贷余额11%的增长率。建行房贷的增长率,在国有大行中名列前茅。
横向来看,建行房贷余额在全部上市商业银行中,无论是绝对额,还是结构性占比均为行业内最高。2020年,建行房贷余额5.8万亿元,超过工行1000亿元;结构占比方面,建行房贷占全部贷款的比例约为35%,超过工行4个百分点。
利润方面,房贷业务贡献惊人。2020年,建行税前利润的6成以上来自零售业务,由于房贷业务对于零售业务占比巨大,且不良率极低。结论便是,建行赚钱主要靠房贷。
除房贷以外的其他零售业务,如信用卡、消费贷,以及个人经营贷等业务,2020年底余额1.4万亿元,占比不足20%(占全部贷款仅为8%),尽管去年有近20%的增长。显然,在零售业务领域建行没有形成自己真正的竞争优势,尤其跟同行相比的时候。
这一格局的形成,一定程度上基于原有业务积累,当然也与新业务拓展的困难度成正比。相比房贷来说,经营贷、消费贷等零售客户的获取难度以及不良率都要大一些,对于风控的要求也高。况且,房贷对于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占用也低一些。这本质上带有监管套利的特点,尽管所有的商业银行都在这样做。